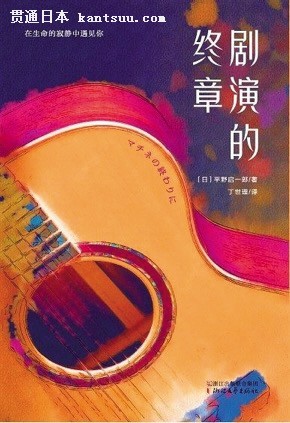平野启一郎(1975-),日本新生代小说家、文艺评论家、音乐人。出生于日本爱知县蒲郡市。大学期间正式开始从事小说创作,23岁时凭借小说《日蚀》,荣获第120届芥川奖,被誉为“三岛由纪夫转世”。
《剧演的终章》 作者:平野启一郎 译者:丁世理 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年3月
《日蚀》 作者:平野启一郎 译者:周砚舒 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年8月 在日本文坛被誉为“三岛由纪夫转世”的作家平野启一郎,年少成名,23岁出版的处女作《日蚀》便拿下了芥川文学奖。他的小说题材不一,风格各异,但背后都对应着日本社会的相关问题。近期,平野启一郎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采访,谈论了日本社会,以及如何通过文学来介入社会现实等话题。 对立与分裂的时代里重新审视爱情 新京报:《剧演的终章》跟你以前的小说不太一样,它是一部以爱情为主线的小说,为什么会想创作这样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 平野启一郎:其实在过去的作品当中,也有写到爱情。完全以爱情为主线,这次是第一次,但是我一直想创作这样一部作品。我感觉读者可能也希望能有这样一部作品。因为现在的社会也好,经济也好,政治也好,这些现实可能会让读者有点疲于奔命。所以我希望至少在我们读小说时能有一种美好的感受或体验。还有一点是,我去找自己想看的爱情小说,但是找了一圈之后发现好像没有,那我就自己来写。我也希望我写的作品是自己想要读的那类小说。 可能在整个社会当中,大家更多地强调对立与分裂的存在,或许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一下爱这个主题。我所说的爱不仅仅是爱情,更多的是父女之间的亲情,师徒之间惺惺相惜的感情,又或者是恋人之间的,有很多种形式的爱存在。 新京报:《剧演的终章》是一部比较治愈的小说,我听说你提出的“分人理论”在日本也救了很多想自杀的人,给了他们勇气。在整个社会都比较丧的氛围下,你为什么会有这么积极的一面? 平野启一郎:因为对处于比较艰难的境遇中的人来说,你只是单纯地跟他说加油,这可能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所以作家对自己的语言是被怎样理解的、对希望对方积极生活下去的这些语言应该予以重视。所有我用“分人”这一概念,会让这些读者看到,人生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观察角度,他们也可以对自己过去的人生做一次再整理,产生与以往不同的想法,从而成为改变自己生活的一个契机。我认为比起一味地鼓舞对方的精神,这样做会更有意义。 比如说,有些人在学校或职场过得不太顺利,可能在过去,他会觉得我整个人都做不好,否定自己的整体。当他听完有“分人”的概念之后,他会发现在职场上的我是其中一个人格,跟朋友和家人相处是另一个人格,我并不讨厌那部分的人格,我就可以获得另一个全新的视角。 自由意志很重要,但个人命运会被时代改变 新京报:《剧演的终章》另一个比较突出的主题就是人的命运,小说里的洋子是一个比较相信自由意志、痛恨虚无的人,你本人对命运的看法是不是也是如此? 平野启一郎:我也看中国的文学作品,包括我很喜欢的一部作品——余华的《活着》。《活着》描绘了整个社会的背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主人公的命运其实是被时代潮流所捉弄的。 日本在二战后一直处于民主和资本主义盛行的社会背景之下,大家认为每个人都是有自由意志的,但实际上现在日本社会有一些贫困的人存在,很多人觉得他们穷是因为自己没有努力,完全是自己的原因,而不是社会造就的。而实际上,虽然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很重要,但处于时代大背景下,个人的命运是会(随着时代)有所改变的。我希望通过《剧演的终章》中洋子这个女性角色来反抗日本当下的你是自由的、所以你不好的经历完全是自己导致的,这样一种价值观。 新京报:我看到一个调查数据,说高达百分之六十三的受访者“对参加游行有抵触感”,而这个比例以二十到三十岁的人为主,年轻人好像参与社会运动与政治的积极性不高?这是不是就是你小说里写的个人面对社会的无力感? 平野启一郎:可能过去人们说日本属于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大家的收入水平都在中产左右,但实际上日本现在的贫富差距是比较大的,一些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没有办法接受更好的教育,所以他们有很大的几率会过上低收入的一生,他们的子女也会重蹈覆辙,持续好几代,导致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趋势逐渐形成。 像我这样40多岁的日本人,被称为是“失落的一代”,遭遇了就业的冰河期,现在过的生活也不是特别景气。我10岁到20岁之间时,日本正好处于泡沫经济期,经济形势非常好,所以对我们来说经历了两个时期的对比,我们会认为过去是好的,现在是坏的。但对于日本年轻一代,也就是20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从出生开始经历的就是经济低迷期,对他们来说,整个状况没有任何变化,没有所谓的好坏。所以去参加一些游行活动,想要改变社会的现状,变得像以前一样好,这对他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共鸣。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不想去参加游行。 但想要强调一点,现在的年轻人也是有两面性的,因为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整个日本社会对未来都是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比较悲观。也会有一些年轻人想要改变这样的现状,他可能并不是想要使经济形势变得更好,而是希望改变大家期望找稳定的工作、变得比较保守的现状,所以也有人参加游行,以达到自己的诉求。 新京报: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里讲到,要解决低欲望社会的问题,解决劳动人口不足,关键是建立一个移民社会。日本确实也放宽了引进外来劳工的政策,你是怎么看待建立移民社会这个建议的? 平野启一郎:日本政府目前在表面上好像并没有制定非常多的移民政策,但它会以很多不同的名目引进外国劳工来作为日本劳动力的补充。但这些外来劳动力的生活水平是非常低的。比如在签证的政策中会规定他们不能带自己的配偶和家人来日本,所以他们的生活不能说非常幸福。如果不去改善这种状况,大量的这类劳动人口会对日本社会抱有不满。如果政策上不做调整,去很好地缓解或保障这些人的生存条件,而仅仅把他们当做一种劳动力,一种外来务工人口引进的话,对社会来说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会造成动荡,甚至会让政府付出更大的代价。我认为不应该单单只把这些人看做劳动力,而是应该在政治、政策方面思考如何让他们更好地和日本人一起在日本社会生活,不然会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 另外,他们在日本的工资和待遇比较低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这样下去,日本会变成让外国人觉得是一个很难在此工作的国家。如果劳动力不足,只是想着单单引进一些劳动力来补充,可能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作家应用语言艺术,表现灾害 新京报:我知道你本人在比较积极地介入社会,包括反核电,好像还参加过几年前在国会前的反安保法抗议活动,能不能聊一下你的看法和感受? 平野启一郎:当时为什么反核电?第一,核电已经带来了很多的灾害,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第二,日本的劳动人口逐渐不足,所以日本政府现在找一些低收入国家的人,让外来务工人员处理核电废物,它其实是一件很不人道的事。过去宣传核电非常低成本,是经济效益比较好的一种能源,但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谎言。核电站既缺乏经济合理性,又会造成这么多不人道的事情发生,核泄漏之后还有很多人被迫过着避难生活,没有办法回归到正常的社会生活跟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没有理由不反对。 关于国会前的抗议活动,我认为现在的国会属于保守派,甚至可以说成是极右翼,我是很崇尚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所以我需要把自己倡导的东西表达出来。 新京报:《剧演的终章》里也写到了东日本大地震,这好像成了日本很多电影和文学的主题。你觉得在这样的大地震面前,文学应该怎样发挥它的作用,或者说怎么去记录这种灾难? 平野启一郎:如何在作品中触及自然灾害,有很多种方法,有一种是纪实文学,把它真实的情况记录下来,当然这不仅限于记录自然灾害。比如说核电事故;比如说在东北地区为了防止海啸,会在沿海建很多防波堤等等。日本有许多文学作品都触及了这些灾害事件。就我而言,我认为在自己作品当中表现人的生死观念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比如你非常钟爱的人,他突然间有一天因为一个突然的事故去世了,这可能会对人的生死的观念有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我的朋友里有一个是律师,他去受灾地区给灾民提供法律咨询,比如给失业者或是家被冲走的这些受灾群众提供法律咨询。但那个朋友对我说,作为志愿者为他们提供这样一种法律咨询服务是很重要的,但对灾民来说,他们最需要的还是让他人理解自己的处境,能用一些语言讲述出他们的遭遇。所以我的朋友有时会觉得自己的法律咨询服务对灾民可能无法提供很大的帮助。对灾民而言,语言的力量可以说变得十分重要,所以作家应该通过语言的艺术去表现和描写灾害对灾民的伤害以及灾民的遭遇,从而发挥自己的一定的作用。 采写/新京报实习记者 聂丽平 |
平野启一郎 在日本,多数人看不到明朗的未来
新闻录入:贯通日本语 责任编辑:贯通日本语
相关文章
日本前幼儿园职员涉嫌偷拍男童并贩卖视频被捕 涉案人数逾500人
牛丼连锁“すき家”母公司年营收破1万亿日元 创日本外食业纪录
前佐贺市议因利用高龄女性认知功能下降骗取4145万日元,被判刑6年
日经平均股价一度上涨超过800点,徘徊在38,400点以上
日本千叶外房海岸发生连续冲浪事故,2人不幸遇难
香川老旧天文台举办最后一次观测会 望远镜将移至博物馆展出
日本和牛出口额创新高
日本福岛地方社区再造计划获成效
日本青少年自杀率下降得益于心理健康项目
日本企业女性管理层比例首次突破15%
外国人劳动政策放宽以应对劳动力短缺
日本推出新育儿支援政策应对少子化
鈴木えみ、夫との寝室別スタイルを告白「いびきがすごくて一緒には絶対寝ない」
倖田來未、ロサンゼルスで大胆スリットから美脚披露
武田真治、コスプレで別人級の変身!
ジェジュン、「ビジュアルショックだが、私はイケメンだとは思わない」
IVEユジン、故郷・大田でKリーグのキックオフセレモニーに挑戦
NewJeansダニエル、ファンへの感謝と不屈の決意を綴る長文メッセージ
(G)I-DLE、グループ名を「i-dle」に変更し新たなスタート
日テレ郡司恭子アナ、『ミヤネ屋』で結婚を生報告
本仮屋ユイカ、「名前で負けた」と感じた芸能人を告白
島袋寛子、透明感あふれる最新ショットが話題「白に白を重ねたような白」
川瀬もえ、愛車シビック公開で話題沸騰「渋い」「カッコよすぎ」
国民民主党、参院選候補者選定で「身体検査不足」への懸念が浮上
工藤静香、長女24歳誕生日に色鮮やかなワンプレート料理を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