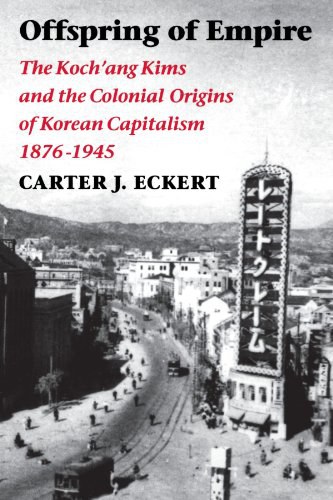当地时间2020年10月25日,韩国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在首尔的三星医院去世,享年78岁。虽然自从他于2014年突发心肌梗塞之后,公司事实上的管理已经由其长子李在鎔负责,但这位三星帝国二代掌门人的逝去还是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2020年10月28日,韩国京畿道华城,路边纪念李健熙的标语。 与中文媒体对于李家“继承者”们的豪门恩怨以及韩国财阀与政府新一波权力斗争的关注相比,日本舆论的焦点则更倾向于李会长与本国长期以来的密切关系。除了大众媒体全方位的报道之外,在第一时间就做出反应的还有私立名校早稻田大学。早大在李氏去世隔天就发布了一份声明表达对于他的深切哀悼。作为该校65级第一商学部校友的李健熙不仅在2010年被授予了早大名誉博士的称号,而冠了他姓名的政治经济学图书馆在早大众多的学部图书室中也以设施的先进闻名。另一方面,韩国最大财团曾经的掌门人在日本接受高等教育且有着深刻的人脉绝又绝不只是个例。举近的例子来说,同样在今年初去世的乐天集团会长辛格浩(日语名重光武雄)在2017年接受韩国法院关于偷漏税审判时用日语大喊“谁敢判我”可能只是坊间传闻,但他儿子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带着浓重日语口音的韩语以及在签订重要文书时总使用日本名的事实不时触动韩国网民的神经。以李健熙为代表的韩国经济界与日本想切却又无法切断的关系背后有着更为深刻和复杂的历史原因。它们不仅在微观上左右了单个企业的成长,更在宏观上以包括“日韩贸易战”在内的各种形式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韩国经济的殖民起源说 与全书主体部分冷静的议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哈佛大学教授Carter J. Eckert在其著作《Offspring of Empire》(暂无中文版,参考日语译名「帝国の申し子」在此译作《帝国的赐子》)引论部分情绪鲜明的批判。这本1992年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图书奖受赏作品的主要焦点是日本殖民时期朝鲜半岛的资本主义发展史。Eckert的攻击对象是在当时韩国学界作为主流的所谓“萌芽派”。这些学者认为半岛的资本主义早在17和18世纪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萌芽”)。比如,开城等地的人参商人很早就拥有了遍布东亚的销售路径。根据这种思路,日本自1876年《江华条约》开始的对半岛的渗透乃至最后的吞并被认为是阻碍半岛经济发展最大的要素。Eckert指出对于在殖民期间事实上存在的半岛经济的长足发展,这些学者们要不是选择轻描淡写,要不就是只把焦点放在所谓百分百由本国人控住的“民族资本”之上。在他看来,这种被民族主义裹挟的史观是对事实的无视。在把工业化视作现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征之后,他开始了自己对韩国经济殖民地起源的详细论证。
《Offspring of Empire》书封 根据作者的观点,在日本统治期最早获得收益的是当时的地主阶级。本来就拥有大片土地的他们在参与到了对日本的粮食出口之后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资金积累。但在早期,这些保守的地主还是偏向于把收益用于进一步的土地收购。而在1919年之后,地主们的投资才开始逐渐向工业倾斜。这种变化和宏观上的政经结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在国内,虽然在1910年的《日韩合并条约》之后,朝鲜半岛彻底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但日本的高压统治在第一个十年显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1919年席卷全境的“三・一”独立运动让当局不得不采取更为柔性的政策。在经济上,随着旧《公司法》在1920年的废除,原本处处受限的本地资本也开始进入工业领域。与此同时,在日本本土接受高等教育的地主后代在此时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人力资本”。而在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导致的粮食价格下跌更是给地主们把闲散的资本转移到农业之外提供了额外动力。由此,朝鲜半岛的资本主义开始走上快速的发展道路。 在《帝国的赐子》一书中,Eckert教授聚焦的核心事例是出生于今天韩国全罗北道高敞郡的金氏一族,特别是金性洙和金季洙两兄弟。他们两个人的发展轨迹可以说完全符合了上述半岛资本家们的简史。兄弟的父辈靠着祖上的土地在殖民开始后逐渐获得翻倍的土地和资本。被送去日本并分别在早稻田和京都大学学习的两人回国后正好赶上殖民当局的开放政策并以股份制的形式开创了京城纺织株式会社(简称“京纺”)。对于许多韩国学者来说,金家的案例不时被当成日本殖民下“民族资本”的代表来进行讨论。但Eckert却反其道而行指出了在京纺背后无处不在的日本参与。不管是京纺的成立初期还是业务拓展期,只靠金家来自土地的积累不足以让公司在几乎是被来自日本本土的纺织公司所垄断的半岛市场站住阵脚。京纺三种最主要的资本来源:股份,补贴和银行贷款都得到了当时朝鲜总督府的大力支援。不仅许多殖民高官都持有公司股份;而且总督府的资金补助一度达到京纺总资本的四分之一;最后以有官方背景的朝鲜殖产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又在公司发展的每一步给京纺提供保障。到殖民结束的1945年,朝鲜半岛的工业总产值比重从1910年代的2.9%成长到了近四成左右。 当然,Eckert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殖民主义辩护。虽然和当局的合作让许多民族资本家取得了迅速的成长,但结构性的不平等也注定了他们无法和日本企业在一个公平的市场展开竞争。上文提到的京纺只能生产已经被追求精细化的日本纺织业淘汰的次级布料,而无法在南部的大城市吸引到客户的公司只能独自在日本资本还没有完全进入的北部农村甚至是中国东北寻求市场。 《帝国的赐子》自然不是一本完美的书。比如,不少学者批判作者没有考虑到许多在当时成功的民族资本在经历了朝鲜战争之后都不复存在的事实。从而,把现在韩国经济的成功和日本殖民直接联系在一起有失偏颇。但另一方面,即使单个的企业延续不得不中断,殖民期所留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日本资本扮演的角色显然没有轻易地被政治变动而打断。在此,以三星为代表的韩国企业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 三星奇迹的日本要素 虽然许多殖民时期的大企业在日本战败后失去了往日的荣光,但借着“汉江奇迹”而起的韩国新财阀也并不是从战后的“真空”中诞生的。韩国最主要的三大财阀:三星,现代和LG在殖民时期就已经开始发家。而虽然不同的统计方式可能有细微差异,但许多报告都显示至少到上世纪80年代为止韩国一半左右的企业其创立者都有着日治时期地主阶级的出身。
李健熙(右)与父亲李秉喆的合影。 三星集团的创始人李秉喆就于1910年2月12日出生在庆尚南道的大地主家。虽然他比上文提到的金家兄弟的资历晚了十年,但他成长的轨迹却和他们惊人的相似。1929年入学早稻田政经科的李秉喆在日本本土学到了先进的管理知识。回国后的他选择在本土产业还拥有较大发展空间的马山以一家精米所开始了自己的商业生涯。发展初期,虽然有着来自同胞的资本合作,但他仍然离不开朝鲜殖产银行的金融支援。和这些官方机构的良好关系也成为了他能够从一众小企业中脱颖而出的一大原因。中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李秉喆以大约现在三万韩元的资本开创了主营贸易的“三星商会”。利用日本殖民者在半岛和中国东北修建的先进基础设施,三星和其他贸易公司即使在战争中也取得了稳定的发展。 学者李惠美则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三星在战后发展及其中日本影响更为详细的梳理。根据她的介绍,1948年11月,三星物产公司正式设立。但公司的营业随机在朝鲜战争中收到重创。即便如此,早在1950年,以三星为代表的韩国经济界就已经来到日本进修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并和仍处在百废待兴状态中的日本企业结成了良好关系。 1951年1月,李秉喆在釜山重新开张。意识到相比于不稳定的货物进口,自己主动生产更为有效的三星从1953年开始逐渐进入砂糖、纺织等输入替代产业。虽然公司需要的资本大部分可以从国内的市场以及政府补贴中获得,但工业不可或缺的技术没有日本的帮助是行不通的。在三星的要求之下,日本三井物产不仅为集团旗下的第一制糖设计了总工程规划,实际运行中重要的生产设备基本都是从日本原装进口。而其后三星的肥料工厂更是接受了三井近4190万美元的支持,成为了当时韩国国内最大的工程项目。在硬件之外,李惠美还提醒我们注意到企业所不可或缺的软性制度。三星从50年代开始模仿日本战前的财阀对组织内部进行再构筑。1959年,公司仿造三井集团在总部设置秘书室。通过它,当时集团旗下17个子企业发展方向的制定和互相之间的统合变得更为顺利。 从1960年开始,李秉喆每年的年始年末都会在东京度过。通过和日本各界的沟通,他得以在第一时间把握全球市场最新的动向。李惠美在论文中引用相关报道指出三星在当时做出进入电子产业的决定正是在三洋电机会长井植岁男的强烈建议下才逐渐成型的。在新的十年中,三星通过成立合资公司成为了“汉江奇迹”的核心发动机。而日本一国的企业就占到了所有合资公司数量的一半。这也显示了在1965年日韩恢复外交关系后两国业界更为密切的合作。同样的,在此期间三星对日式制度的学习也进一步加深。在李看来,最为重要的无疑是可以在多个产业领域同时负责原料、商品进口和外销的日本型“综合贸易商社”。在伊藤忠商事的领导人濑岛龙的建议之下,三星也拟定了自己的方案并向当时的朴正熙政权直接上书。1975年的5月19日,“三星物产”正式成立。虽然此后经营的内容有所增减,但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三星财阀众多企业中核心的组成之一。 进入80年代,随着韩国经济走上正轨后,企业对日本的依赖有所减少。而从三星开始进入半导体产业之后,两国之间更为直接的竞争和对立也越来越多发。但要说日本要素完全消失却也不是事实。1987年正式接班的李健熙继承了父亲的传统就读早稻田。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要想日本学习的他积极引进了日式在职教育为企业储备人才。即使在韩国看似打败了日本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存储芯片出口国的今天,该产业也无法完全摆脱作为其部分原材料近90%的原产地的日本。这一现状加上前述的历史也成为了仍在进行中的日韩贸易战的结构性原因。
2020年11月2日,韩国首尔,三星电子举行公司成立51周年纪念活动。 从“黑名单”到“白名单” 如前所属,《帝国的赐子》的作者认为1919年是半岛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为了平息民众的独立诉求,朝鲜总督府不得不在包括经济之内的各领域开放更多的机会给被殖民者。但他也同样提醒我们,试图把民族资本家拉拢到统治的核心从而分化半岛民众其实是这一策略的另一面。虽然我们无法确定民族资本家们与殖民者的合作多少是出于真心想要“卖国”,多少是因为形势所迫,又有多少是抱着想要“曲线救国”的企图。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与当局的合作在战前给他们带来了实质的收益而在战后让他们惹上了看似是无穷尽的麻烦。 在今天的韩国政坛,给对手贴上“亲日派”(在韩语里这三个汉字所包含的批判意味远大于中文语境)的标签无疑是最好用的攻击手段之一。对于这些在日本统治期间背叛民族的殖民合作者们的讨伐其实早从战后不久就来开了帷幕。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大韩民国初代总统李承晚在任期内就通过了《反民族行为处罚法》并在1948年10月开设了反民族行为特别调查委员会。特别裁判机关一共整理了559件事例,其中221件被起诉,最终包含死刑在内共有12人被判刑。但李承晚的清算在当时政权并不稳固且南北对峙加深的情况下显然不够彻底。此后韩国不稳定的政权更迭让相关问题没有再次得到系统性讨论。但在韩国社会,特别是民族主义者之间,对“亲日派”的讨伐不曾中断。他们最常用的一种手法就是发布各式各样的“亲日名单”。比如2002年的2月国会内的“民族精气议员会”就发表了总共包含708人的“亲日派”名单。2005年8月,民间团体民族问题研究所更是出版了包含3090名“亲日家”的大词典。其中收录的人物上到首相、参谋长,下到画家甚至是韩国国歌的作曲家,可谓涵盖了殖民社会的方方面面。 很快,对于“亲日派”的梳理超出了“纸上谈兵”的范畴。2004年3月,卢武铉政权通过了《亲日反民族特别法》从而得以在政府层面认定民族叛徒。2005年底,国会更是制定了《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国家归属特别法》。只要被改法认定为在韩国独立前靠着反民族和反国家行为而取得的财产都将被没收。即使大部分当事人此时已经去世,法律仍对继承了他们遗产的后代适用。2007年5月2日,财产调查委员会宣布将没收包括签订了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的李完用等9名“亲日派”及其后代的财产。这批共154笔、25万多平方米的土地时价约达36亿韩元。此后,委员会又几次追加新的“亲日”黑名单以及待没收的财产。自然,韩国国内并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该法是否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以及违反了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的意见时有提出。根据2015年KBS的报道,仅当时在委员会和“亲日派”及其后人之间就有96起诉讼。而在已结案的94起中政府获得了91次胜利。就在今年8月,《中央日报》还报道了民间团体光复会表示又发现41笔亲日派的新“不义之财”并上报韩国法务部。这也告诉了我们该议题远还没到彻底解决的时候。
2018年10月30日,韩国首尔,韩国最高法院判决新日铁住金(日本钢铁公司)向二战期间被强征的4名韩国劳工每人赔偿1亿韩元(约合61万元人民币)。 殖民时期留下的深刻问题当然不会只通过“黑名单”的形式对国内经济造成影响,日本统治的“负遗产”还始终是两国之间政经摩擦的来源。从2018年底开始,韩国的司法系统判决了一系列与日本殖民时期经济相关的案件,并要求包括三菱重工、不二越与日本制铁三家公司支付被强征的工人们至少每人8千万韩元的赔偿。2019年的1月和3月,韩国地方法院判决同意没收日本制铁在韩股份以及三菱在韩部分资产的决议。这些案件其实都有着漫长的审议过程,而此时的集中宣判以及对日本企业利益现实的损害让日本政府再也坐不住了。在日本看来,1965年两国恢复国交时已经彻底解决了相应的历史问题。韩国通过接受来自日本的三亿美元无偿资金援助、两亿美元有偿贷款以及三亿美元的民间借款就放弃了进一步赔偿的诉求。对于当时一年国家预算只有3.5亿美元的韩国来说,这笔及时雨无疑为日后所谓的经济“汉江奇迹”打下了物质基础。但随着韩国民主化以及民族主义的升温,这一政府之间协议的合法性越来越被质疑。来自韩国个人针对日本企业的诉讼成为了让两国政府都棘手的问题。作为这次的报复手段,日本政府抓住媒体报道韩国有敏感物资流出的事件在去年8月正式将该国移出了自己的贸易“白名单”。这意味着原本无需审核的可被用于武器制造的材料现在需要逐项进行申请,其中就包括了对韩国芯片制造业来说至关重要的原料。而不甘示弱的韩国也把日本从自己的贸易优惠国“白名单”中除去。国内随即爆发的一波波抵制日货的运动至今都没有完全平息。而就在日本刚释放出将限制出口的消息没过去几天,当时三星的副会长李在镕就立刻飞抵东京。有媒体报道他近一周的拜访十分成功。尽管具体的斡旋细节没有公布,但可以推断三星集团和日本财界长期以来的合作关系让公司得以在两国掣肘的特殊时期也能有效缓冲自己的损失。 即使在因为疫情影响世界各国的经济表现都不理想的情况下,日韩之间的经济摩擦似乎也没有要彻底终结的意思。有不少评论家都站出来呼吁“让经济的问题回归经济”。确实,不管是历史上的“民族资本”还是当下掺杂了“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似乎都让单纯的经济问题变得复杂化。但回过头来说,这种呼吁多少也有些过于理想化。纵观历史,真的只靠纯粹的供需关系来调节的交易根本只存在于经济学家们的模型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存在纯粹的“经济问题”,任何的经济学都必须是“政治经济学”。 除非历史可以重新来过,日本的“殖民遗产”永远是两国需要靠智慧去博弈并寻求平衡的对象。 参考文献: Eckert, Carter J., Offspring of Empire : The Koch'Ang Kims and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Korean Capitalism, 1876-1945,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1, 08. 李恵美, サムスングループの形成と成長における日本からの影響, 国際日本研究, Vol.8, 2016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
从三星会长去世到日韩贸易战:日本殖民遗产如何影响韩国经济
新闻录入:贯通日本语 责任编辑:贯通日本语
相关文章
没有相关新闻